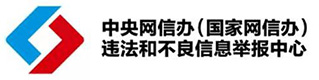我的法官情结
当我身着黑色的袍服在审判席上耐心听讼的时候,当我苦口婆心给当事人做工作调解的时候,当我冒着凛冽寒风在乡间寻找送达地址的时候,当我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和心情回到家里的时候,我偶尔会回想起自己是怎么成为一名法学的卑微朝圣者的。也许是2000年,报纸上登出了新的法袍式样,那一袭黑色就映在了我的心里;也许是高一那年,班长拿出了一个小小的录音机,让我们在跨世纪的这一天记下自己的理想,莫名的,“最高院的院长叫肖扬,我要做法官杨潇”脱口而出,从此,“法官”二字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。
美国著名学者德沃金在《法律帝国》这本书对法官形象有着精辟的描述,“在法律铸造的帝国里,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,而法官则是帝国的王侯。”,大学时,我为此对崇高而威严的法官职业油然产生了几多神圣,几多向往。四年法学理论和西政精神的浸淫,“博学、笃行、厚德、重法”的校训犹在耳际,我已经面临就业选择了,为了心中无限的憧憬,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法院。犹记得第一天到法院报道时的情景,从审判庭虚掩的门缝里,我看到了一位法官坐在高高的法官椅上,神情专注,仔细倾听当事人的陈述,轻轻点头或者微锁眉头。庭上,弥漫着紧张、威严的气氛,那名法官掌控庭审的张力,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。近三年的法院工作生涯,让我理解到“法官”二字更为深刻的涵义。
民事庭法官刘忠新,明年就要退休了,他已经审判岗位上坚守了数十年,如今仍然战斗在审判任务最为艰巨的民事审判前线。经常已到下班时间了,他还在办公室与当事人耐心长谈。就这样反复找当事人沟通协商,苦口婆心地做双方工作、不厌其烦地讲利害关系、深入浅出地释法说理。以循循善诱的话语、锲而不舍的精神,促成当事人的和解。他手写的判决书通常是长达十几页公文纸,工工整整,并且凭借着自己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,努力做到“辨法析理,胜败皆明、输赢皆服”。法院像他这样的老同志还有很多,他们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都默默消耗在了呕心沥血的秉公执法上、无私为民的排忧解难上,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,他们依旧悄无声息地燃烧着自己,散发最后的光与热。
聂河法庭庭长汪娟娟,作为我院唯一一位女性派出法庭庭长,辖区却是条件最为艰苦的三个乡镇,然而她却以瘦弱的身体为山区百姓撑起了一片公平正义的蓝天。那还得那天,快到下班时间了,她风尘仆仆地来到我的办公室,急冲冲地拉着我就走,路上我才了解到她是想请我和她到银行去查账,可能是帐户有误,那天一无所获。看着着急的样子,我心想:这可能是个大案吧。于是,我答应她第二天等她从聂河开完庭出来再去查。第二天下午,我们顺利地查到了被执行人的帐户,可我仔细一看,上面竟然只有七百多块钱,我笑着对她说:“你看你费了这么大的劲,就为了这么点钱啊?”,汪娟娟一愣,说道:“我们山区能有多大标的的案子啊,不是离婚就是赡养案件,就这750块钱还是我磨破了嘴皮子才执行来的半年的抚养费啊!”。当那位申请执行的老人颤巍巍地接过几百块钱,眼里边含着泪说:“多亏了汪庭长啊,为了孙子的生活费,我每年都要麻烦她几次,但她总是不厌其烦的为我做工作,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路……。”这位老人的话在我的脑海里回响了许久,我为自己的肤浅而感到脸红,却也再一次感受到法官职业的沉重。
也许法官都是普普通通的人,所做的那些事都是很平凡事。但是,他们却懂得“虽不是每一个诉求都能如愿以偿,但耐心倾听、真诚工作却暖人胸膛”。善良的微笑,使多少心灵得到慰藉;真诚的话语,给多少弱势群体送去关爱;谦和的态度征服了多少桀骜不驯的当事人;同情的泪水,给多少久旱的心田播撒下公正的甘霖!
当我第一次成功调解了一桩纠纷的时候,当我精心制作了第一份判决书让当事人的权益受到保障的时候,当我看着当事人接过标的款那感激的笑容的时候,我又再一次坚定了我的法官情结,我明白了,既然我选择了这条艰辛的路,我将终生用自己的辛勤跋涉,去感受法的脉动与心率,去探寻法的精神与真谛,用自己的操守捍卫着法律的公正,用自己的生命捍卫法律的尊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