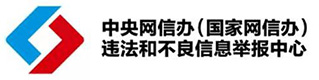厂房拍卖背后的千人生计
——我的“放水养鱼”破局之路
桌上的案卷还带着油墨的余温,甲、乙两公司与丙公司的工程款执行案,昨天正式画上句号。这不是一起简单的“要钱”案,而是一场关乎近十家企业存续、上千人饭碗的“保民生”之战。作为承办此案的执行法官,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走进丙公司厂区时的震撼,上万平的厂房里,机器轰鸣,工人忙碌,谁能想到,这片厂房的所有人,早已因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,官司缠身、账户冻结,不得已将厂房出租取得相应收入,只留下几名留守人员维持基本管理。
干执行,第一步就是“摸家底”。线上查控系统火力全开,线下跑不动产、工商…一趟下来,我惊喜地发现丙公司名下还有上万平的厂房,以及少量机器设备,“有财产可执行,这案子应该不难”,当时我还跟同事念叨了这么一句。
然而当我去丙公司所在地走访调查时才发现情况比预想的更复杂:上万平的厂房和少量机器设备,早已设定了多项抵押,厂房也已经租赁给了多家规模企业生产经营。
我站在厂区的过道,看着来来往往的工人和货车,心里瞬间沉了下来:按传统执行思路,拍卖厂房设备是最直接的办法,可真这么做了,这近十家承租企业就得立刻腾退,他们的利益如何保证?上千号工人的饭碗如何保证?那些正在生产的订单又如何保证?就算最后厂房拍出去了,拍卖款扣除在先的抵押债权,轮到甲公司和乙公司,还能剩几个子儿?这哪是执行,简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,搞不好还会引起社会风险。
愁归愁,案子还得办。既然厂房动不得,那丙公司有没有其他收入?挨家走访承租企业后,我了解到丙公司有一定租金收入,但均转入丙公司指定的高管个人账户。
找到线索,我立刻拟了协助执行通知书,想让承租企业把租金直接打到法院指定账户。可没想到,第一家企业的老板就拒绝了我:“不是我们不配合,水电气、厂区安全都是丙公司管,我们要是把钱给法院,它要是断水断电找我们麻烦,我们怎么办?”
承租企业的担心不是没道理,我没再硬劝,转身就去找丙公司的留守负责人老王。在他的办公室,我拉过椅子坐下,没提执行的事,先听他倒苦水。得知丙公司早就停产了,就靠租厂房收点租金,可账户被冻结,连留守员工的工资、社保都快发不出来了。等他说完,我才慢慢开口:“欠债还钱天经地义,但法院也不是要把人往绝路上逼。要是能靠租金慢慢还债,法院可以帮你们留足必要的开支,让公司先‘活’着,总比厂房被拍卖、大家都没出路强,你说对不?”
我让老王把这话转达给丙公司负责人,还留了我的手机号:“有想法随时联系我,咱们一起商量。” 没过几天,老王就给我打了电话,说公司愿意谈,并准备提交《分期履行申请》。
在《分期履行申请》中,丙公司表示愿意将所有租金收入交由法院监管,但希望留下50%用于支付必要开销(工资、社保、税费、水电、办公费),剩下50%用来偿还债务,并承诺两年内还清所有欠款。
起初听到这个协议,甲、乙两公司都是不情愿的,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,毕竟换谁被欠钱都不好受。
我耐心解释,“竭泽而渔的典故两位老板肯定不陌生,现在榨干丙公司账面上的租金,不出意外它立马就会倒闭,到时候厂区一乱,租户退租,厂房贬值,抵押都覆盖不了,你们的债权更难保障!反过来,试着‘放水养鱼’,让它维持基本运转,租户安心生产,租金源源不断,你们的债权才有保障。”双方最终达成和解,“用租金收入的60%偿还欠付工程款,剩余40%租金返还被执行人维持公司的正常经营。”
拿着这份协议,我再次走进厂区。这次,我把协议内容、法院的监管职责,以及丙公司承诺保障租户正常经营的义务,都跟租户们讲得明明白白。大家心里的石头落了地,纷纷承诺:“法官放心!租金我们一定按时足额打到法院账户!”
自那以后,租金成了“活水”。每次款项一到账,我们都严格按照协议,雷打不动地第一时间将60%划给债权人,40%返还给丙公司。流程透明,分毫不差。目前,甲公司工程款及滞纳金已全部收回,案件执行完毕。丙公司厂区内各企业活力运转。乙公司债权正在按和解协议履行。
这个案子,让我对执行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,作为执行法官,手里握着强制执行的利剑,但更重要的,是要有洞察困境的慧眼和促成共赢的担当。本案中,“杀鸡取卵”固然干脆,但往往一地鸡毛;“放水养鱼”需要耐心和智慧,却能换来生机盎然。面对企业,尤其要精准区分“恶意逃债”和“诚而不能”,真正让债权人的权利有着落,让诚信企业能“喘口气”,让上千人的饭碗端得稳,这才是“善意文明执行”理念最生动的诠释,这也是刚结完这个“热乎”案子,我最真切的感受。